【编者按】
2021 年 6 月 20 日至 23 日,“沐浴党的光辉 追溯百年风华——崇德尚艺 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巡回宣讲”走进湖北武汉、江西上饶。中国剧协顾问、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罗怀臻全程参与活动,他在活动现场谈到,“可能也是因缘际会,波动了我们内心的某一个敏感的神经,使我们对某项工作、某项事业、某种文化创造产生了兴趣,这种兴趣逐渐演变为我们的责任与担当,最后成为使命,一旦成为使命,它就要带领我们所的这个行业、专业,在这个时代去攀岩新的高峰。这个高峰既是对前人创造的当代总结,也是留给后人的一个标杆。”此番肺腑之言引起了现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考和共鸣,恰与 2020 年 11 月“艺苑百花”对罗怀臻的专题深入报道不谋而合。现将第 28 期“艺苑百花”《罗怀臻: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使命》采访文章进行摘登。
罗怀臻: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使命
多重身份感:寻找更多同行者
●中国艺术报:长期以来,您主要是以剧作家的身份为人们所熟悉,但逐渐地从创作向戏剧教育、社会动领域拓展,并有很多触及重大问题、现实热点的理论思考及发声。您怎么看待这种不同的身份感和自己走过的路?
◎罗怀臻:多重身份感的形成,还是跟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。我们每一个身处在一个时代、一个时期中的人,都不应该仅仅是某一个单方面的技术人员,还应该有一个比较开阔的视野、具有宏大背景的意识。回过头来,这都有利于他做微观的、具体的事业。从剧作家的身份来说,我当然很欣赏古代的关汉卿、李笠翁、汤显祖,也很欣赏我们前辈,像田汉、吴祖光、曹禺这样一些文化人。他们尽管都有第一身份——剧作家,但是他们通过剧作,同时也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探索和追求,传达出了时代的文化精神。他们是一个个杰出的剧作家,又不局限在剧作家的身份上,所以他们做得更好,并且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。我不是刻意在剧本创作的同时去研究理论、从事教学,去推动行业的发展。归根结底,还是因为我觉得,仅靠一己之力去一个一个地写剧本,我觉得不够了。因为我写的剧本,它也存在着舞台呈现、同行沟通协调等方面的需要;那么,我所追求的剧作精神,能不能获得更多的同行者呢?它能不能影响我们的文化决策者而更好地推进行业发展呢?出于这些原因,我才兼顾到其它的一些门类或部门。虽然我有戏剧界的行业身份,也有教职,甚至也管理着一个部门,但是我真正的身份,还是剧作家,为了把剧作家的身份做得更好,所以兼顾到其它的方面。
三个创作阶段:为生存、为文学和为理想
●中国艺术报:回顾您早年从表演走向戏剧文学创作的历程,从最初的出发地到如今不同身份的转换,时代语境毕竟已有很大的变化,对照自己的选择,您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?
◎罗怀臻:我个人的艺术创作,尤其是戏剧创作,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:第一个阶段就是为生存的创作。我 16 岁作为知青插队,20 岁重返城市。重返城市的通道,就是进了地方戏曲剧团。为了生存,我进剧团做演员,后来兼而写剧本。但是,一旦进入这个职业,尤其是当戏剧创作逐渐成为我的主业,我就希望在表演中、在舞台艺术上,能够更多地灌注文学的内容。我的第二阶段,就是为文学的创作。因为我在剧本写作之前或者更早的时候,我就喜欢读文学作品。我主要的阅读积累是在 13-20 岁之间。13 岁那一年,我很清晰地记得,我读了三个让我终身难忘的作品,第一部是曹禺先生的单行本话剧《雷雨》,第二部是中国话本小说《说岳全传》,第三部是雨果的小说《九三年》。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一个 13 岁的小孩抱着这样的文学名著在阅读,而且我读进去了,直到今天,我觉得我的生命人格和我的创作风格当中,细心的人都会发现,我依然不能摆脱这三部作品的影响。文学在我的知识背景中,在我的阅读记忆中,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将来会成为作家、剧作家,但从13 岁开始的阅读,到 20 岁,但凡中国名著、世界名著,唐诗、宋词、元曲,包括中国的民间文学,我能看到的,都是如饥似渴地看。一直到了 80 年代,这样的阅读一直延续着。
再民间化和再乡土化:找回古朴源头的生命力
●中国艺术报:您所说的源头回归,是不是讲回归艺术所蕴含的那种最原初的生命力?
◎罗怀臻:其实它最本质的东西,是地域文化。因为地域文化,某种意义上还承载着民族文化。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,甚至汉族本身,也是从非常多元的状态演化过来的。无论是行政区划还是地域版图,都有自己的地域传统和人格图谱。就像我们理解江南,往往以为就是阴柔秀美,好像强悍是属于北方的;其实不对的,江南人格是中国人人格当中非常强悍的。当年江阴抗清,全城就仅存 50 多人,都战死了;扬州、嘉定、松江、宁波这些地方,也很壮烈,陆地上不能坚守了,漂浮到海上,继续坚持战斗。这才是江南人格,是很强悍的。像绍兴,那是复仇之邦,是出过越王勾践的地方;项羽揭竿而起,江东子弟,那也是江南。今天我们要回归、要寻找,就是要找回这种东西。我们今天常听越剧,特别是女子越剧,觉得是江南的;可是真正的高腔是在江南,你看那个绍兴大班,我们的《女吊》,包括金华、温州,都保存着大量的高腔。声腔的背后,其实是一个地域的气质。在今天的城市化、都市化进程中,这些带着远古的身份感、地域感的剧种、声腔、方言,它逐渐被同质化了。我们要显示今天文化的多样性,就要找回这些东西,找回它古朴源头上的精神气质。越是现代化、都市化、国际化,往往就越应该显示出对我们各自文化来路、精神气质的回归和复兴。所以,到了《武训先生》,我提出了再乡土化,其实它的精神跟之前提出的都市化是一样的——都市化是路径,再乡土化是手段,最后实现的就是让淮剧更淮剧。
姓氏背后的秘密:族群和血缘记忆终将沉淀为一种生命气质
●中国艺术报:这让我想起您对多重身份的自我定位,跟社会身份不一样,地域文化背后的内涵也很有意思,比如您是河南人,出生在江苏,对此您是怎么看的?
◎罗怀臻:跟同时代的很多剧作家略有不同,我参与过的剧种可能相对是比较多的。什么才叫参与了?不是你去写了,就叫参与了,你得带着剧种的感觉,写了属于剧种的剧本。这可能跟我的人格血缘身份有关系。我出生在苏北,但从童年开始,我在苏北就有一种异乡的漂泊感,为什么?因为我的祖籍是河南许昌,它不仅仅是我心灵记忆中的一个原乡,而是我在 4 岁到 7 岁时,我真的被过继到我乡下的大伯家生活了三年,这恰恰是一个人种植记忆、种植味觉、种植美感甚至是决定一生意识的一个时期。我一直以为,我是一个出生在江苏的河南籍人,每年我去河南,都会去祭扫祖先。可后来我发现,我也不是中原人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有一个姓氏起源告诉我,我的家乡许昌和周边的洛阳、开封,这一带的罗姓,其实是鲜卑族的后裔,是北魏孝文帝进入中原以后实行汉化的结果。当地罗姓是由鲜卑族的一个氏族——叱罗氏,经汉化改过来的。这一度成为我的一个心病,我到哪里去证实呢?前不久,我去了一趟内蒙古,专门参访了拓跋珪的纪念馆。进去之后,在墙上的一个鲜卑族汉化演进表中,我赫然看到叱罗氏就是后来的罗姓,我刷地眼泪就下来了。在我的个性当中,在我的作品当中,不少研究者说,他的作品像上海的?不像;像苏北的?不像;像楚文化的?不像;像中原的?都不像。这里边就像有一种宿命的、浪漫的东西在支配着,最后我找到了它游牧民族的根——我自己的血,血性和血液埋伏在自己的身体里上千年了,祖先的基因没有磨灭掉。那一刻,我一下子就释然了。我在内蒙古待了几天,我的感情,我的自我意识,都变得清晰了然。我想自己今后的创作,都可能会因这种明白而更加自觉。
地域文化想象:海派是永远在动荡中,不断地打破纪录
●中国艺术报: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、也是您一直推动和践行的戏曲现代转化的课题。
◎罗怀臻:这就是作家、艺术家的使命,感受、理解并建立自己的观念、理想,然后去实现它。王安忆、张爱玲的使命,就是传达上海的东西。我觉得,每个作家、艺术家都有与生俱来的使命,就是你必须做,做完了就拉倒。像路遥一样的,就给你那么多时间,你必须把《平凡的世界》写完,所以他把命都搭进去。陈忠实也是,给你一个使命,把《白鹿原》写出来。这种感觉,我现在找到了,我也有这种野心,来传达上海的,又不止于传达上海的。我欣赏的那种海派,是周信芳式的海派、赵丹式的海派、黄佐临式的海派、越剧十姐妹式的海派、俞振飞式的海派。我愿意把我放在海派的坐标上。我觉得,海派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感、承载现代性的东西。用今天的话讲,就是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就是守正创新、返本开新。其实说到传统、说到基本功,还有比周信芳、赵丹、袁雪芬、黄佐临、俞振飞他们更扎实的吗?无需多说,一目了然。经典对于他们来说是参照,不是目标。海派就是以古今中外的经典为参照而非目标,然后形成一个很高的参照系,作为自己的发力点,不是要成为什么,而是要创建什么。这是我理解中的海派,也是我对戏曲现代转化的理解。京派是要成为什么,然后吸收、归纳、提纯、定型,并影响了一个时代,因此不断地创造纪录,然后让你去模仿;海派是永远在动荡中,不断地打破纪录,它们是不完全一样的。
常态的思考:一直都在现场,一天都没离开过
●中国艺术报:这几年您出版自己的剧作集、演讲集、研究集和教学集,每一部分都是很有分量的几卷本,比较系统地概括了您的职业经历、艺术生涯和成就,其中有什么契机吗?
◎罗怀臻:并非刻意设计,不经意间它们就完成了。从 60岁这一年开始,我陆续得到了几个渠道的出版资助,我就把它们用来出版我的著作。在出版剧作集的时候,我不知道后来会出版演讲集,出版演讲集的时候,我也不知道后来会出版研究集,出版研究集的时候,我也不知道我会出版教学集,可就是在两三年间,四套文集出版了,每一套都是三卷本 120 多万字,整整 500 万字。它很神奇地来到我人生的 60 岁,不经意间做了一个小小总结,概括了我的生命履历和 30 年来辛苦的写作。12 卷文集的出版,让我心里有了一种平和感,我觉得对得起我生命的 60 年和写作的 30 年。从个人来说,无愧平生。但是,伴随着一点点成就感,我也有一点点悲怆感,就是感觉文集出版了,以后多写一个剧本都是赚的,多写一篇文章也是赚的。现在我读关汉卿的剧作,其实很想看到关汉卿的言论、看到关汉卿的情感,我很想看到他在一个个作品演出时所遇到的困难,可是我看不到。我今天比关汉卿幸运,就是我不仅留下剧本,我也留下了围绕这些剧本的思索和时代的印记。它们可能会是路标,为我的同行者、传薪者、后来者,提供一个可以看到的机缘。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到今天,在我 30 多年的写作过程中,有的人走在我的前面,有的人在这条路上出局了、不干了,有的人变成了发牢骚者。不管时代怎么变迁,提倡历史剧创作也好,提倡现代戏创作也好,提倡开放也好,提倡复古也好,我都在现场,一天都没有离开过现场。
(节选自“艺苑百花”专题第 28 期,责任编辑:刘金山,编辑:张桐硕)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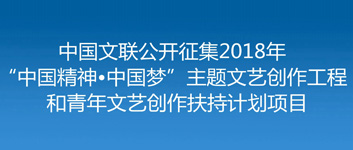
 中国文联公开征集2018年度文艺创作扶持项目
中国文联公开征集2018年度文艺创作扶持项目